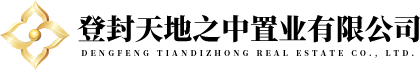王石:中國與美國、日本的經(jīng)濟差距有多大?
近日,萬科董事局主席王石在接受《中國慈善家》雜志專訪時,通過對比中外發(fā)展歷史,表達(dá)了對時局的看法。他說:“如果你說明明是在走回頭路,那我告訴你,這是黎明前的黑暗,是大變革時代即將到來。”
在哈佛大學(xué)研究美國和日本之后,王石更認(rèn)為中國還是很有希望的。
王石對比發(fā)現(xiàn):中國現(xiàn)在急速地城市化、工業(yè)化,這種狀況和美國100年前有著驚人的相似。也就是說,我們現(xiàn)在并不比美國當(dāng)時做得更壞,不用垂頭喪氣。我們搞市場經(jīng)濟,搞經(jīng)濟增長,就會破壞環(huán)境。新英格蘭地區(qū)急速工業(yè)化、城市化過程中,93%的水土流失,當(dāng)時的環(huán)境破壞比我們還厲害。
但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(chǎn)生了世界第一個國家公園—黃石公園。我們不是比較他們和我們表現(xiàn)得一樣壞,而是要參照借鑒他們的做法。參照借鑒的不是現(xiàn)在,而是100年前,借鑒他們怎么走過來的。
“而中國到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時,城市化率低于1949年,整個倒退了。你會發(fā)現(xiàn),現(xiàn)在這次城市化過程中,中國已經(jīng)沒有退路,不可能再走過去的道路,城市化道路必須走下去。
從這個角度看,中國是非常有希望的,不用擔(dān)心任何回頭路,因為沒有回頭路可走。”王石說。
企業(yè)家掌握主流話語權(quán),應(yīng)推動社會改革
問:在微博上,你經(jīng)常發(fā)布各類植物和小動物的照片,作為這方面的愛好者,是否可以從這里找到參與環(huán)保事業(yè)的源頭?
王石:沒有直接關(guān)系。個人微博這兩年有較大改變,因為房地產(chǎn)不太好談,很敏感。對于花花草草的關(guān)注,跟我的個人興趣有關(guān)。我對植物,第一比較感興趣,第二和業(yè)務(wù)有關(guān),綠化環(huán)境本身是小區(qū)規(guī)劃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倒不是跟環(huán)保有什么直接關(guān)系。但是對個人的修養(yǎng)多少有關(guān)系,個人對有生命的植物、小動物都不去關(guān)心、關(guān)注,也就談不上對大自然的熱愛了。
談到環(huán)保,涉及一個人的行為,首先人是自私的,最關(guān)注的是自己,首先應(yīng)該強調(diào)這個。不要一談個人愛好就都和公益有關(guān),都和企業(yè)有關(guān)什么的,其實是沒有關(guān)系的。但實際上,自私對我來講一定是利他的,就是利己到最后演變成利他。因為關(guān)心花草、關(guān)心小動物,這些都不是孤立的存在。最后一定形成一種共識,關(guān)心生命。如果你對它不了解、不關(guān)心,你來唱高調(diào)—關(guān)心環(huán)保、關(guān)心自然,一定是空洞的。你不利己,第一我懷疑你的誠信,第二即使你很真誠,但能持續(xù)嗎?
問:2008年,汶川地震后,因為一句“普通員工限捐10元,不要讓慈善成為負(fù)擔(dān)”,你被卷入輿論漩渦。對于自己當(dāng)時的理性表達(dá),現(xiàn)在怎么看?
王石:隔著時間去看越看越淡。我遇到那種情況,壓力非常大,負(fù)面輿論大,心里想不通。但現(xiàn)在再回過頭看,那個事反而比較簡單。既然做公益,本身被誤解,不被接受,這很正常。當(dāng)然當(dāng)時不會這么想,只能事后來看。在中國做公益,公共空間本來就不夠大,傳統(tǒng)的中央政府大包大攬一切,民間的公共空間很窄;現(xiàn)在到了公民社會,更多的公共空間由民間來做。既然是走在前面,言論錯對是一回事,本身就會遭到質(zhì)疑、誤解。
至于說到一個人的行為,我的體會是兩點。中國改革到現(xiàn)在,更多由官員、學(xué)者考慮、推動,我們作為社會的一員,作為企業(yè)家,現(xiàn)在又掌握著主流話語權(quán),應(yīng)該在社會改革上面推動。社會改革就是不但把自己的企業(yè)做好,還要體現(xiàn)企業(yè)公民的責(zé)任。
我去金沙江漂流,有一個非常深的體會。金沙江是長江的一個支流,漂流又是在懸崖峭壁之間,我發(fā)現(xiàn)一種現(xiàn)象,峭壁上都是一股股涓涓流水,你會感覺到,滔滔長江、金沙江就是涓涓細(xì)流匯合而成的。我們每個人就是一股涓涓細(xì)流,如何讓社會更美好—我們是抱怨呢?是等著中南海來決定、來改變呢?還是首先從我們自己做起?如果每個人都從自己做起,社會自然就改變了。
這么多年,我找到了做這些事情的感覺。能力有大小,你盡自己的能力,你是企業(yè)家當(dāng)然要盡企業(yè)家的能力。這就是我自己應(yīng)該扮演的角色,不要更多地想著這應(yīng)是別人做的,應(yīng)該上面去做。這是我的最大體會。
問:你在哈佛大學(xué)研究資本主義發(fā)展史,怎么看19世紀(jì)末、20世紀(jì)初大企業(yè)家紛紛成立慈善基金會做慈善?他們是在為原罪贖罪嗎?
王石:這個原罪說是我們中國的解釋邏輯,我在美國并沒有體會。他們沒有原罪——我的掙錢能力是上帝賦予的,我掙的錢是替上帝保存。
既然是為上帝保存財富,那他們遲早要離開這個世界,要到上帝那兒,去之前財富怎么處理?第一,本身有一個如何分配的問題,分配后還有一個問題:后代拿這么多錢有什么好處,這反而是個困惑。第二,遺產(chǎn)稅很高,所以成立基金會是讓財富通過上帝的意志關(guān)心窮人、做公益活動,宗教有這樣的一個含義。第三,政府鼓勵有錢人做這些事情,在稅收方面有優(yōu)惠政策。第四就是社會的需求,財富進行第三次再分配。
至于在中國,我覺得就很難說。
問:現(xiàn)在很多民營企業(yè)家也開始捐贈財富做慈善,例如曹德旺。這是否意味著他們的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,也會將財富轉(zhuǎn)為社會影響力?
王石:有待觀察。為什么呢?中國改革開放到現(xiàn)在30多年,民營企業(yè)家的積累還是很有限的,再加上中國的發(fā)展機會很多,會把更多的積累作為原始資金投入擴大再生產(chǎn)。在這個過程中,你讓他們把錢都捐出來做公益基金,顯然對企業(yè)發(fā)展不利。最起碼在未來20年到30年之間,民營企業(yè)家出現(xiàn)像曹德旺這樣的慈善家只是個別的現(xiàn)象。
中國的財富積累之后,怎么進行社會再分配。我個人也有點疑惑。因為發(fā)展到現(xiàn)在,我覺得有幾個問題。民營企業(yè)創(chuàng)造的財富到底算誰的?這很含糊。當(dāng)然你說法律上非常清楚,是個人的。但觀念、本質(zhì)上是很含糊的。就是說個人的財富并沒得到很好的尊重,個人財富沒有得到尊重,那就不是他的。他考慮的不是捐出去,那就轉(zhuǎn)移。確定是我的,我最后才能決定捐或作什么其他處理。
比如2008年,大家對我的那種態(tài)度,就是你應(yīng)該捐啊,你什么意思,你不就賺倆臭錢嗎?現(xiàn)在國家有大災(zāi)難,你不捐誰捐?這個邏輯很簡單,是很可怕的事情。所以企業(yè)家賺錢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,不會捐出去,而是想辦法轉(zhuǎn)移出去。你說為什么現(xiàn)在移民熱?這是很重要的原因。
中國很多事情是民情比法律還要大,要不怎么“不殺不足以平民憤”。這很可怕。民憤并不等于對的啊,是不是?要尊重法律,尊重契約精神,要不民憤就不可捉摸了。
問:如此說,慈善的大發(fā)展在某種程度上受制于民眾對財富的態(tài)度。
王石:如果不弄清財富到底是誰的,公益活動就不可能健康發(fā)展。在美國,非常非常清楚,財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,我的就是我的,至于我怎么得來的,只要不違法,都要尊重。要不最后非法的也是合法的,最后就是掠奪。沒有私人財產(chǎn)神圣不可侵犯,他都不能做到很安心的自私。不利己,怎么利他呢?利他也是一種迫不得已。
中國應(yīng)向美國學(xué)習(xí)的,除了創(chuàng)新還有責(zé)任
問:阿拉善SEE生態(tài)協(xié)會在民主治理上建立了一套良好的機制,這應(yīng)該是企業(yè)家的一個主要貢獻吧?
王石:參加阿拉善協(xié)會是企業(yè)家自身民主自治建設(shè)的過程,而且我個人認(rèn)為,這種建設(shè)本身的意義超過具體項目。當(dāng)然,搞公益基金會要有項目支撐。阿拉善更多的影響是企業(yè)家如何約束、自律,如何進行民主自治建設(shè)。我們強調(diào)民主、公平,如果我們在自身的組織中都不能有一套民主的公平的程序,我們又是社會主流的資源控制者,那么如何要求這個國家、社會進行公平地建設(shè)?所以在這方面,妥協(xié)的概念非常重要。
問:跟民主是相關(guān)的。
王石:對,民主本身就需要妥協(xié)。
問:你多次強調(diào)加入阿拉善SEE生態(tài)協(xié)會之后,你學(xué)會了妥協(xié)。妥協(xié)的更大意義在哪里?
王石:在中國的公益活動中,妥協(xié)是非常重要的。所謂妥協(xié),簡單來講,就是不要把你的意志強加給別人,不要認(rèn)為你什么都是對的,要更多聽別人怎么想、每個人怎么想,之后把每個人的想法融合到一起,讓大家都能接受。中國人的生活中,這是非常缺少的,尤其是現(xiàn)在社會轉(zhuǎn)型當(dāng)中。
問:在你看來,中國民營企業(yè)家專程去美國學(xué)習(xí),不僅學(xué)習(xí)開拓創(chuàng)新的意念,更重要的是學(xué)習(xí)對社會責(zé)任的擔(dān)當(dāng)。在這方面,民營企業(yè)家與美國企業(yè)家相比,差距主要在哪里?
王石:我們所指的距離,一是方法論,再一個是觀念。
方法論當(dāng)然有差距,但主要的差距還在觀念上。舉個例子,我們現(xiàn)在認(rèn)為要效率就得專制,民主就沒有效率。在美國開會,我有語言障礙,一個專題發(fā)言需要用準(zhǔn)備好的稿子去念。
但是自由討論,有時候跟都跟不上,肯定記不下來,要點都不知道說什么,你怎么談觀點?那不行,既然我邀請你參會,你一定要發(fā)言。這點我印象非常深刻。我們這邊發(fā)言,同意不同意大家都贊成,要不就兩邊吵得一塌糊涂。他們不是。你參加會是因為你的身份,因為有你的價值存在,你講什么不重要,但一定要說話,一定要表達(dá)。
所以你會發(fā)現(xiàn),在那兒開會兩三天,未必有什么結(jié)果。因為首先他尊重你,沒有什么大佬發(fā)言定調(diào),沒有。我覺得這種觀點最起碼是對人的尊重,對每一個人的尊重。現(xiàn)在中國非常欠缺這個。如果沒有這個,即使有再好的方法論、再好的工具,也很難判斷,方法論是建立在這個觀念基礎(chǔ)之上的。
我原以為民主的效率很低,后來發(fā)現(xiàn)別人已經(jīng)很成功了。是有效率低的,但人家把每個人的主觀能動性都發(fā)動起來,每個人都表達(dá)自己的觀點,這些人就心甘情愿地去執(zhí)行。而我們這邊是,想得通得執(zhí)行、想不通也得執(zhí)行,我們都是帶有強制性的。所以咱們學(xué)什么?我覺得更多來講還是觀念:每個人都有他的權(quán)利。
大變革時代即將到來
問:在哈佛大學(xué)訪學(xué),除了知識上的學(xué)習(xí),還受到哪些獨特的訓(xùn)練?
王石:任志強說,王石去哈佛,是受教育不夠。別人怎么看不重要,我非常接受他這個說法。我是受教育不夠,我的英語都要從口語開始,難死了。我上的很多課都是本科生的課,不是博士、碩士生的課。但我聽得津津有味,因為我沒有受過這樣的系統(tǒng)訓(xùn)練,我受的訓(xùn)練是工農(nóng)兵,很多教育非常僵化、教條。我這兩年在哈佛受到了基本的訓(xùn)練,非常受益。
所以任志強的話出于什么動機不重要,我非常接受那句話。我就是受教育不夠。但是,受教育不夠的僅僅是我嗎?不斷挑戰(zhàn)自我、超越自我的人不多。不僅僅是受教育不夠,西方的方法論和東方的方法論都是智慧,但是不一樣。
為什么現(xiàn)在關(guān)于中國的現(xiàn)代化,人們吵來吵去?他們在沒有受西方訓(xùn)練的平臺上,說的根本不是一件事。爭來爭去始終在那打轉(zhuǎn)。所以我為什么非常贊成方舟子,方舟子的訴求不重要,你喜歡不喜歡也不重要,但他跟你爭論的方法論,是受過西方非常嚴(yán)格訓(xùn)練的。而國內(nèi)很多完全就是不講道理。但講理對不講理,總還得講理。
問:你在海外訪學(xué),主要研究內(nèi)容是歷史學(xué)。而你一直喜歡歷史學(xué),哪些歷史學(xué)家的著作讓你受益良多?
王石:歷史學(xué)對我的影響有幾個階段。
第一是湯因比的《歷史研究》。是我剛到深圳時讀的,到現(xiàn)在還記得。它告訴我,任何歷史的發(fā)展都有一個過程,同時歷史有相當(dāng)?shù)呐既恍裕皇潜厝恍浴S辛诉@種認(rèn)識,如何認(rèn)識自己的民族、如何認(rèn)識自己的國家,可以進一步提高自信。
第二是吉本的《羅馬帝國衰亡史》。參照羅馬,對比中國現(xiàn)在發(fā)生的情況,你會驚訝地發(fā)現(xiàn),雖然是2000年前的歷史,卻與現(xiàn)在有很多相似之處,而制度、民主、方法論上,我們還不如2000年前的羅馬,我們現(xiàn)在的制度設(shè)計比他們還要落后,就更不要說和現(xiàn)在進行系統(tǒng)比較。認(rèn)識到差距,反而坦然了,而不是灰心失望。
第三是到哈佛之后。我研究美國、日本,從傳統(tǒng)到近現(xiàn)代,如何城市化,如何工業(yè)化,感覺中國還是很有希望。
問:希望在哪里?
王石:中國現(xiàn)在急速地城市化、工業(yè)化,這種狀況和美國100年前有著驚人的相似。也就是說,我們現(xiàn)在并不比美國當(dāng)時做得更壞,不用垂頭喪氣。我們搞市場經(jīng)濟,搞經(jīng)濟增長,就會破壞環(huán)境。新英格蘭地區(qū)急速工業(yè)化、城市化過程中,93%的水土流失,當(dāng)時的環(huán)境破壞比我們還厲害。
但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(chǎn)生了世界第一個國家公園—黃石公園。我們不是比較他們和我們表現(xiàn)得一樣壞,而是要參照借鑒他們的做法。參照借鑒的不是現(xiàn)在,而是100年前,借鑒他們怎么走過來的。
日本是第一個完成工業(yè)化和現(xiàn)代化的非西方國家,它是怎么完成的?這就是為什么我研究江戶時代的原因。在明治維新之前,他們的社會是什么狀況?你深入進去會發(fā)現(xiàn),它已經(jīng)做好準(zhǔn)備了。這你得服氣它。不是說殖民性、侵略性,打了兩次戰(zhàn)爭把中國打敗了,占了賠款,我們衰落了。不是這樣的邏輯。
江戶時代的國民掃盲運動、國民教育已是全世界最好,甚至高過德國、英國和荷蘭。而我們到1949年,不要說1860年代,差不多過去80年之后,我們的文盲率還在80%左右。而日本在江戶時代就已結(jié)束了,男子掃盲運動后文盲率50%,女子掃盲運動后文盲率25%。也就是說,日本女子的掃盲遠(yuǎn)遠(yuǎn)超過中國男子的掃盲。這就是農(nóng)業(yè)文明時代的日本工業(yè)化在全世界最高的原因。
而中國到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時,城市化率低于1949年,整個倒退了。你會發(fā)現(xiàn),現(xiàn)在這次城市化過程中,中國已經(jīng)沒有退路,不可能再走過去的道路,城市化道路必須走下去。從這個角度看,中國是非常有希望的,不用擔(dān)心任何回頭路,因為沒有回頭路可走。如果你說明明是在走回頭路,那我告訴你,這是黎明前的黑暗,是大變革時代即將到來。